



在的后台留言中,有读者希望我们写一写罗伯特·艾格斯的新版《诺斯费拉图》,其实在看完后,我们都陷入了沉默。
能够理解艾格斯从《女巫》走来,一直试图以男性视角为出发点,投入女性主义的叙事当中。你不能说他不努力,但这个命题就像让熟读波伏娃+伍尔夫+上野千鹤子的男性去测评卫生巾——不是努力就有用的。
作为哥特文学史当中的典型意象,吸血鬼在经历过千禧文化的普世解构之后,已然从嗜血的恐怖生物,成为更适配乙女文学的完美情人。不生不灭被引申为永葆绝世容颜,附加几辈子攒下的雄厚财力;嗜血本性则可以优化成不食用人血的素食主义,外带一种危险的性暗示。伫立在流行文化中,备受追捧的吸血鬼们,已然失去了恐怖感。
Make Vampires Scary Again的任务交到罗伯特·艾格斯的手上,本该是令观众安心的,然而事与愿违……


新版《诺斯费拉图》的影像风格,被艾格斯赋予了有别于历任表现主义特色的古典式悲剧感。即使我们很难忍住对剧本的诟病,也不得不承认影片的光影质感很出色。


摄影师Jarin Blaschke掌镜了《女巫》《灯塔》《北欧人》多部艾格斯代表作,在本片中,他也将艾格斯对于“黑暗”的理解赋予可视化的诠释。艾格斯希望借助影像语言,呈现“黑暗”的本真状态,因此在摄影上,Blaschke有意过滤了红、黄、绿等色彩,保留了在黑暗环境中,最大限度接近人眼有限可视的灰蓝色调。直至影片结束,女主艾伦与诺斯费拉图相拥而逝,以最明快的姿态迎接与拥抱死亡本身,黑暗才被曝露在暖色之下。


但这仅仅是影像语言最大程度上对故事的服务,回归剧本,我们仿佛观看了一部吸血鬼版《危险方法》+《哈利·波特与密室》。除了对原作照本宣科般地推进剧情,艾格斯似乎将诺斯费拉图与艾伦之间的牵绊,定义为世俗与信仰双重压抑下,女性(甚至男性)欲望的走火入魔。
诺斯费拉图倒不像是着迷于鲜血,而是借助“吸血”这一带有性暗示意味的行为,间接服务于艾伦的本能需求,甚至顺便服务了艾伦的丈夫托马斯。这和《哈利·波特与密室》里仿佛初代Chat GPT的日记本,倾听与安抚金妮的少女心事殊途同归。而诺斯费拉图卡在喉咙口的呓语,怎么不算一种蛇佬腔?


对于艾伦的所谓治疗和驱魔,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柯南伯格的滑铁卢之作(之一)《危险方法》,只是给艾伦带来实质性疗效的并非荣格与弗洛伊德,而是无证行医的诺斯费拉图伯爵。
稍显悲哀的是,即使是被扁平化为歇斯底里症患者的艾伦,已经是全片当中,逻辑与行为整体相对最自洽的角色。其余角色的行为动机,仿佛都随着对原著的尊重这个借口,而被带入了赶场一般的怪圈。

如果艾格斯再大胆一点,把电影的名字从《诺斯费拉图》改成《艾伦·亨特传》,虽然故事依旧糟糕,但至少可以减掉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罪名。
甚至当我们转变心态之后,会发现故事的逻辑也通畅了不少。前半程花了这么大力气,无外乎给艾伦确诊歇斯底里,让诺斯费拉图成为女性被压抑的欲望的具象化。上一次看见这么上赶着给别人确诊的桥段,好像还是《卖拐》。只不过艾格斯的野心不只是把人忽悠瘸了,还得摁着人的脑袋,让人家承认“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都精神多了”,由此升华到献祭艾伦、以扼杀诺斯费拉图与瘟疫的大和谐。怎么说?还是学医救不了人对吧。


新版《诺斯费拉图》对艾伦刻意为之的去污名化,恰恰反证了在这个故事,或者大多数吸血鬼题材作品当中,女性角色的扁平与被禁锢。她的欲望即便被正视,她的身份即便被认同,她即便可以拯救全城,所必行的途径仍然是老套的色诱。这种看似性别尊重的表达,其实有点像除夕年夜饭时,男性长辈举起酒杯祝酒,“让我们恭喜今天在这个家里,女的可以和我们男的坐在一桌吃饭了”,会有人觉得这是真诚的祝福吗?很难吧。
以往的《诺斯费拉图》及其他吸血鬼作品中,女性角色往往被塑造为迷茫的、脆弱的个体,是男性角色或幻想、或保护的对象。在当下的语境之下,观众所诟病的并非女性角色的行为,而是对角色自主意志的漠视,使其缺乏作为人应有的欲念以及逻辑。艾格斯在新版中的尝试,也仅仅止步于合理化了女性角色的七情六欲,而没有继续深入追问,艾伦的病灶究竟在哪儿。对女性叙事的偏重,也折戟在“我不要你觉得,我要我觉得”,比起聊胜于无,反而更荒诞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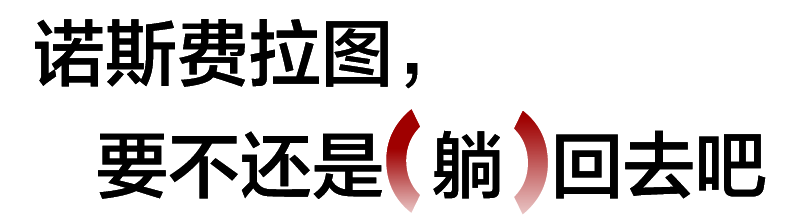
把时间回推一个世纪,1922年茂瑙的原作,如同诺斯费拉图被倒映在墙上,瘦削而扭曲的身影,成为此后的吸血鬼文学与影视作品都很难真正超越的基线。也恰恰得益于原版出现在“电影”这种艺术形式方兴未艾之际,一个带有鲜明恐怖色彩的形象,“生”逢其时。
茂瑙的诺斯费拉图是“恐惧”本身。他从人类身上汲取血液,正如同恐惧在恐惧的土壤中野蛮生长。于是吸血鬼艺术刚刚走到大银幕上,就被平地拔高到了哲学议题的深度。


《诺斯费拉图》(1922)
1970年代的尾声,赫尔佐格的《诺斯费拉图》让我们看到了永生之疾的另一种可能。在他的访谈集《陆上行舟》里,赫尔佐格也将自己的改编版本定义为“一次重生”。他自言作为战后的第一代,自己与同辈电影人是“没有父辈的孤儿”,因此只能继续追溯到爷爷辈的茂瑙或者弗里茨·朗,去寻找所谓“正统”的蛛丝马迹。因此经他诠释的《诺斯费拉图》,主题毫不意外地落在“孤独”。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孤独,看作是恐惧之后的续章,是与恐惧的暗影缠斗过久,自己也变成了一道影子。而不管如何精疲力尽,都如同是陷入了一意孤行的“陆上行舟”。


《诺斯费拉图:夜晚的幽灵》(1979)
是不是诺斯费拉图在2020时代,已经失去能够重生的土壤?
新版《诺斯费拉图》的差强人意,或许并不应该全部归咎到艾格斯,而是吸血鬼题材一再“下沉”之后,已经被解构成了一系列空乏的标签,难以重回哥特艺术的本质,变得很难更有趣了。这也很像诺斯费拉图离开古堡,远渡重洋,却最终在新世界水土不服。他预言了他自己的命运。
说“XX已死”固然矫情,但与其以当下视角进行所谓反观,剥皮去骨,重新解读,还不如让那些特定土壤诞生的诺斯费拉图们,死在他该死的年代。这样一来,也就不必再苛责《惊情四百年》是正宗科波拉味儿的“老登电影”,再指指点点《夜访吸血鬼》的两位主角,如今千疮百孔邋遢不堪的戏外人生。


《惊情四百年》(1992)
艾格斯翻拍的《诺斯费拉图》,好像一个削足适履,最终无所适从的失败试验品。要坚持标志性的艺术风格,又要在数个原版以及相似题材的基础上,寻找一种新的可能;要沿袭原版作品的精神内核,又要顺应舆论和流行的风向,强行贴合更当下和安全的主题。要不负众望,又要搞搞新玩意。最终的结果是,他拍得疲劳,观众看得无趣,互相折磨两小时。
诺斯费拉图伯爵,还是躺回棺材里吧。


 支付宝扫一扫
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