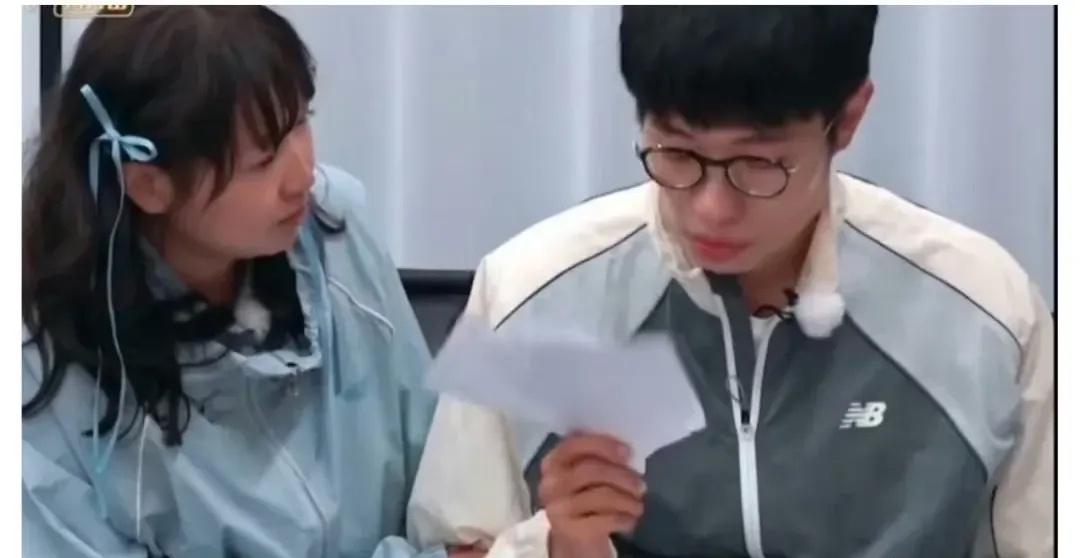有人说2024年的内娱天降紫薇星是麦琳,从“青团事件”到“画像奔溃”,从“我配拥有一杯咖啡吗”到“熏鸡事变”,她能够轻易引发众多现象级话题,被网民称为“先天抽象圣体”。
霎时间,她似乎被放进了网络的“竞技场”中,大众环形而坐,肆意笑谈着。
麦琳解救的不仅有满是“爹”味的“杨子们”,更有早已沉浸在媒介狂欢中娱乐至死的我们。
麦琳,绝望的主妇
“麦琳的出现,让我把杨子都看顺眼了。”
“麦麦肯定是NPD(自恋型人格障碍),简直受不了她。”
“麦琳,让家庭主妇的形象蒙尘,让我彻底放弃女性视角。”
“祝共情麦琳的找到和麦琳一样的伴侣!”
她在想喝咖啡时,摆出极低的姿态却讲出攻击型的用语;在镜头面前不加装饰地展露自我情绪,面对画像自卑时笑出猪叫、单独采访时大哭抹泪;在团队经费不够的情况下强硬要求购买熏鸡,将“坏心眼”和“报复性心理”直白地摊开在公众面前。

图源网络
武志红说,麦琳采用的是“用付出索取爱”的关系模式。她将丈夫李行亮作为自己人生排序的第一位,紧接着是孩子、父母,而自己在这场排序中是最末一名。
于是,在公众面前,麦琳便呈现出一个不断强调自己的付出索取认可、情绪不太稳定易崩溃、让别人痛苦,以此获得共鸣与理解的模样。
“精神PUA”、“表里不一”、“极度自恋”、“吃绝户”等等,是网友为她罗列的“累累罪行”,一时间,她的罪状仿佛罄竹难书。
从长相、学历、性格到口头禅、笑声,无一不被列入审判的范围。

图源网络
在网友的谩骂声中,在迷失自我的困境之中,麦琳,彻底地成为了绝望的主妇。
一场围剿开始了。
赛博猎巫,一场狂欢
网络上对麦琳的讨论轰轰烈烈地进行着,麦琳逐渐成为了形形色色人物的代号,大众将麦琳化身成身边对自己实施“精神虐待”的人物幻象。
网友从其伴侣李行亮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,又在身边开始扫射那些“欺负”自己的人又是否带着麦琳的特质?

图源网络
一时间,人人身边有“麦琳”,人人遭受过“麦琳”带来的伤害,在围猎麦琳这个“女巫”的过程中,大众将日常攒下的憎意与恨意化为“子弹”,射击到麦琳这个独立个体的身上,仿佛身边的“麦琳”也会因此而中弹受伤。
这一口沉闷在胸口的多年郁气,终于爆发了。
网络成为“猎场”,大众以自身的愤怒、痛苦化为利剑,大肆地猎杀他人。“你好像麦琳”成为了用来攻击周围带有其“特质”的人的话语。
麦琳,在当下的网络语境下仿佛不再是一个明确的、具像化的个体,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带有种种坏毛病的攻击性形容词。

图源网络
她成为了电子媒介发泄口,大众在此其中热火朝天地讨论着,乐此不疲地宣泄着。理性思考的能力被抛之脑后,仿佛已全然忘记,这惊涛骇浪般的恶意,这个个体麦琳是否能够承受?
纵使麦琳有错误,却也不应该因为成为网民周围讨厌的人的化身,变成众矢之的。
大众在这场围剿中狂奔着,叫嚣着,丝毫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超出想象。
我们开始沦为娱乐与情绪的附庸。
放大的麦琳,消失的自我
《再见爱人》节目组将麦琳的举动放大,甚至将其标为下期噱头,节目热度高开疯走。在节目组的剪辑下,麦琳却消失了。
一个完整的个体,全面的自我不见了,婚姻生活中的麦琳所呈现的模样成为了她的完整面貌,大众无法得知一个多维度的麦琳到底是怎样的,或许大众也并不关心。

图源网络
媒介使得大众以盲人摸象的方式认识他人,大众便在已经建立的第一印象中通过各种资料的搜集持续认证、深化这一印象。
在“围剿”的狂欢中,消失的不止是麦琳,也是无数参与其中的大众。
1985年,尼尔·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中认为电视等视觉媒介通过情感和感官刺激来传达信息,改变了人们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。
这一观点在当下仍有借鉴意义。
大众在媒介所呈现的娱乐化内容中投放了过多的精力与情绪,逐渐忽略了媒介对个体其实有着很强的塑造和控制作用,我们被娱乐与情绪所裹挟,毫无怨言,甚至心甘情愿。

张婉婷的微博评论
“反感”“不适”“小人得志”成为了社交媒体上讨论麦琳的关键词。大众渐渐迷失自我,忘记了人是立体且多面的,任何一个人站在舆论中心被审判都有可指摘的点。
当任何一个个体站在节目的放大镜之下时,谁又可避免被挑剔?
在一场尽情释放的狂欢之下,全网指责毫无意义,观照自我才是价值所在。引以为鉴,而非围剿,愿大家思考,而不是狂欢。
在如洪流般的流量之下,先别急着奔向下一个围猎场。
更多故事 :
拙见小助手↑
读完记得点个【在看】↓

 支付宝扫一扫
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